【大家】
作者:赵星宇(商务印书馆编辑),韩林合(洪谦弟子、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学人小传
洪谦(1909—1992),又名洪潜,号瘦石,安徽歙县人。哲学家。早年赴日本、欧洲留学,师从维也纳学派主要创始人石里克,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任教,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研究员、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维也纳学派哲学》《论逻辑经验主义》等。
北京大学哲学系珍藏着这样一副对联:“玉宇无尘时见疏星渡河汉,春心如酒暗随流水到天涯。”这副对联寄托着著名学者、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对一位年轻学子的支持与期许。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尽管世界局势风波诡谲,个人境遇跌宕起伏,这位学子始终不负所托,成为我国著名哲学家和哲学教育家。他就是洪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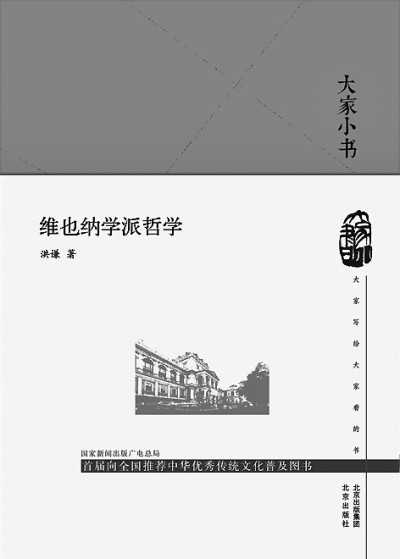
《维也纳学派哲学》 洪 谦 著 北京出版社 图片由作者提供
“维也纳学派”成员
洪谦出生于1909年,是安徽歙县人。他的家境殷实,外曾祖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学者——清朝货币理论家王茂荫。洪谦幼时在福州生活,在启蒙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儒学和新式文化。据其后人描述,少年洪谦曾有一番传奇经历: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王阳明的文章,康有为读到后大加赞赏,便邀请作者前往杭州西湖的花港观鱼处相见,这位维新领袖未料到的是,来者竟是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年。此后,梁启超将洪谦收为关门弟子,推荐他去日本,跟随学术权威宇野哲人学习阳明哲学。
虽然受到康梁的赏识,但洪谦的求学道路异常曲折。由于年纪尚幼,洪谦抱恙从日本回国,待年纪稍长,又前往德国学习,计划跟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教授研究精神生活哲学。可惜的是,1927年抵达德国后才知道,鲁道夫·奥伊肯已于1926年去世。
那时的欧洲,科学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尤其是物理学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样态。天资聪颖的洪谦接触到这些新鲜知识,如获至宝,并且很快上手,只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柏林大学的入学资格,学习天文物理。机缘巧合的是,洪谦在那里参加了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的讲座,并在一次讨论会上做了发言。正如当年获得康梁二人的赏识一样,这位年轻人的讲话吸引了哲学家石里克的注意。从此,石里克成了影响他一生的导师。后来,洪谦随石里克前往维也纳,开启了自己的哲学之路。
石里克早年研究物理学,曾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朗克一起工作,但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哲学,关注现代逻辑以及物理学中的时空观念。作为早期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主要观点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流派不仅非常注重逻辑与概念分析,而且还将最前沿的科学理论扩展到对哲学的反思中。在他们的圈子里,学者们既讨论弗雷格、维特根斯坦一脉对于逻辑、语言的见解,也探讨相对论、量子力学。维也纳学派可谓当时学界的一个浪头,凝聚了多个学科的思想精英,有卡尔纳普、纽拉特,更为年轻的哥德尔、艾耶尔,以及来自波兰的塔尔斯基,这些人在当时和后来都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作为石里克的学生,从1930年开始,洪谦应邀参加石里克小组即所谓“维也纳学派”的周四讨论会,成为维也纳学派唯一来自中国的成员,亲历了它的兴衰。

20世纪80年代,洪谦在北京大学燕东园。图片由作者提供
青年洪谦不仅在学业上受到石里克的指点,生活上也受益颇深。为了锻炼他的外语与信心,石里克派他代表自己出席一些学术活动,引荐他结识学界名流。在洪谦生病期间,石里克还邀请他到自己瑞士的家中休养。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也对洪谦照顾有加,卡尔纳普辅导他数理逻辑,后来成为卡尔纳普妻子的斯托格女士经常辅导他德语。在这样和谐的学术氛围里,洪谦于1934年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完成了毕业论文《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这篇论文的审阅者之一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海森堡,据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尔也参加了他的答辩。
在这篇论文中,洪谦援引当时量子物理学最前沿的成果,反驳了传统哲学中对于因果观念的看法。他认为,有一种关于因果律的迷信植根于经典的物理学和哲学当中,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会将因果原则视为科学知识的前提,也就是为一切知识提供了可能性的东西。然而,面对测不准现象,尽管初始条件、领域条件都已给出,但是人们观察到的结果无法和预测的相同。这也就是说,如果将因果律视为一种必然的、先验的原则,那么当代科学已经宣告了它的破产。需要提示的是,洪谦的见解只是为了消除物理学和哲学上对于因果律的迷信,并不是要将它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他只是希望人们看到:应根据自然规律本身确定科学原理应用的界限,而不是盲目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神话”。在此基础上,他还探讨了事实概率与逻辑概率、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因果秩序与时间秩序等相关话题。
顺利毕业后,洪谦留校任教,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成为维也纳大学为数不多的外籍教师。当时的欧洲大陆被一种怪异的氛围所笼罩,很多年轻人陷入了对政治的狂热之中,一位被精神问题困扰的青年在复杂原因的驱使下,将石里克视为眼中钉,纠缠许久之后将他杀害。这位青年后来被提前释放,加入了奥地利纳粹党。那时,石里克的家人亦受到威胁,他们将石里克的一些手稿和照片托付给作为助手的洪谦,让他保管好这些资料,远离是非之地。多年以后,洪谦访问英国,将这些资料交还给了石里克的后人。

洪谦(中)与石里克(左)、奈德在奥地利。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译文献 守住学脉
几经波折,1937年年初,洪谦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他先是受聘于清华大学,又辗转重庆、贵州和昆明等地,经历过长时间的空袭,遭受过侵略者的殴打,目睹了故土满目疮痍。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洪谦努力向中国哲学界原汁原味地介绍维也纳学派的科学观、哲学观。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哲学不能独立于科学之外,更不是科学的女皇,而是科学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活动,即意义澄清活动。哲学家的世界观的建立必须要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他还全面介绍了维也纳学派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的态度。众所周知,维也纳学派成员对传统形而上学是持批判态度的。在他们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法证实的,因而没有理论上的意义。这样的极端观点不免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维也纳学派企图完全取消形而上学。洪谦在一些文章中欲极力去除人们的这种印象,告诉人们:维也纳学派并不想取消形而上学,而仅仅是要划出它的适当的范围,由此进一步揭示出其本质。他说:“形而上学确能给我们以生活上许多理想和精神上许多安慰。”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应维也纳学派成员魏斯曼的邀请,前往牛津大学任教。或许是因为他在那里介绍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他在国内的家人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阻拦,无法与他团聚。但实际上,洪谦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他只是心地善良,能够理解普通人的苦难,并对那些向弱者施以援手的人抱有好感,他的所言所行,仅仅是凭借他的良知。
1947年,洪谦再次回到祖国,1951年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不仅向国内学界介绍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哲学议题,还着力将其所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会贯通。例如,他探讨了康德星云假说的哲学意义,从科学的角度阐释了其中包含的唯物论、发展观和辩证法等。但是,他的一些观点在那个年代显得不合时宜,遭到了非常集中的批判。加之他不参与任何政治上的斗争,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从此成了一座学术的孤岛。
不过,与当时很多学者相比,洪谦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被北京大学保护起来,性格变得格外谨慎,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人几乎看不懂他的学说,特别是科学、逻辑这些艰深的内容,无从理解,也就无从批判。但是他的学术发展依然停滞了。分析哲学不是玄想的哲学,它的特点除了格外注重逻辑、概念分析,更重要的是很多思考是在论辩与学术交流中完成的,而逻辑实证主义之实证方面,更需要时刻把握科学发展的最新动向。真空的环境使洪谦不再能接触到这些,国内能与他探讨的人少之又少。
种种因素使洪谦不得不专注于编译学术文献。这项工作看似平凡,却为改革开放之后思想文化方面的再次发力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主持翻译的作品不仅包括《逻辑经验主义》,还包括《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等一系列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编译工作之特殊意义,不仅在于为那一代学人提供了难得的珍贵教材和精神食粮,还在于它使得当时教学停摆的学者们有了一份稳定的事业,守住了学脉。那时,作为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洪谦还将大量精力放在了组织工作上,筹备各项事务,亲力亲为。他或许已经意识到,当时的环境并没有发展逻辑实证主义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还因为人们还没有受到过完整的科学、逻辑学和哲学史的滋养。所以,比起在学术道路上踽踽独行,从事编译、教育这些奠基性的工作能给未来的学子带来更多实际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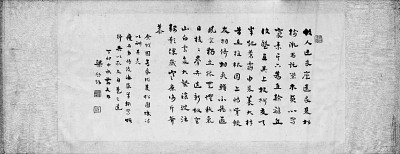
梁启超赠给洪谦的条幅。图片由作者提供
回到国际学术界
改革开放以后,洪谦的学术生涯重新绽放了生机,但再次投入世界的他,感到恍如隔世。他发现,曾经立在潮头的逻辑实证主义,在战后的欧洲已悄然失落,曾经未被足够重视的伦理学成为分析哲学关注的重点,人们开始探讨责任、行动和道义等等话题。更遗憾的是,当他试图重新联系曾经的师长卡尔纳普时发现,他和他的妻子早已离世,而自己只能以悲伤的心情怀念他们,并感慨他们曾经为哲学和社会发展付出的努力。他同情卡尔纳普所持的“科学的人道主义”立场,虽然他们没有机会再相见,但是冥冥之中走上了相似的道路,尽管都走得异常艰辛。
年逾古稀的洪谦仍笔耕不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积极参加维特根斯坦、石里克与纽拉特哲学的讨论会,访问维也纳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等。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担任了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名誉院长,获得牛津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从1987年到2022年,该学院已举办20余届,国内不少从事逻辑学、外国哲学、科学哲学的青年学者都受益于此。
由于对哲学史的重视以及广阔的视野,洪谦对待哲学的各个流派都毫无芥蒂,就学术论学术,尊重差异、兼容并包。这使得他对其他学者的学生也视如己出,所以在他身后,不仅分析哲学、逻辑学的研究者怀念他,从事古典哲学、现象学等领域的后学也怀念他。他们中有的人接受过洪谦的教导,有的人同他一起完成翻译工作,有的人同他交流过德语,有的人曾担任过他工作上的助手,这些学者对洪谦的看法也颇为一致:首先,他治学严谨,从无夸大,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其次,他不炫耀自己的博学,待人永远谦逊。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真诚,坚持自己的学说,并保持独立的人格。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伟在回忆中提道:“他从不戴面具,从不挂脸谱。他从不因迫于某种压力或为迎合某种需要而违心地说话,违心地著文。”这不仅是因为洪谦天性善良,也或许是因为他受过好的熏陶。在他的描述里,维也纳小组氛围和谐,学者之间总是彬彬有礼、友爱诚恳,导师石里克总是有耐心地听完每个人的发言,从不打断。而且,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都未曾被政治浪潮所左右和吓退,他们一生都保有作为学者的高贵精神。
洪谦的一生正应了梁启超送给他的那两句话:“玉宇无尘时见疏星渡河汉,春心如酒暗随流水到天涯。”受时代所限,他的学术成就无法像其他分析哲学、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那样光辉耀眼,他或许只是无尘玉宇中一颗为了渡过宽广银河而历尽千难万险、踽踽独行的小星,但是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韧性,为后世学人留下了宝贵遗产。这些遗产不仅有学术作品、与学生交流时留下的点滴教诲,还有他搭建的学术平台,这些都为中国年轻一代学人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可谓“暗随流水到天涯”。康有为、梁启超、石里克、卡尔纳普这些师长无法陪伴他一生,但他们的精神默默支持着他,滋养了他的心性与品格,而他又用这份良好的心性与品格滋养了后来人。
洪谦的作品不多,但他留下的都是最硬核、最学术的部分。不久前,洪谦的《维也纳学派哲学》作为“大家小书”丛书的一种在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他194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品为基础,书中收录的梁启超赠予他的手书条幅颇值得回味:
故人造我庐,遗我双松树。
微尚托荣木,贞心写豪素。
其下为直干,离立复盘互。
其上枝柯交,天半起苍雾。
由来养大材,首在植根固。
亦恃骨鲠友,相倚相夹辅。
不然匪风会,独立能无惧?
秋气日棱棱,群卉迭新故。
空山白云多,大壑沧波注。
耦影保岁寒,庶谢斤斧慕。
依稀中,洪谦的形象仿佛再现于我们眼前。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8日 16版)
相关阅读:我的导师洪谦先生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