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民学习 向生活学习·重温当代现实主义经典作家】
作者: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孙犁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现实主义作家,深受广大读者和后辈作家同行的热爱。他关注人情美与人性美,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中国抒情传统相结合,书写出了中国农民的新风貌与新形象。作为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孙犁的现实主义写作观是什么,他在文学实践中如何形成他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他留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宝贵财富有哪些?今天,以孙犁为例讨论现实主义传统美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6年孙犁在河北蠡县
他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他是新文学的产妇,要在挣扎战斗中尽了他的任务
1941年孙犁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参加《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对于孙犁的写作生涯至关重要。《冀中一日》是号召冀中百姓人人拿起笔书写“一日”生活的群众性写作活动,在当时的冀中解放区影响广泛。在孙犁看来,“《冀中一日》对上层文学工作来一个大刺激,大推动,大教育,使上层文学工作者更去深入体验生活,扩大生活圈子重新较量自己。在《冀中一日》照射之下,许多人感到自己的文章,空洞无物,与人民之生活、人民之感情距离之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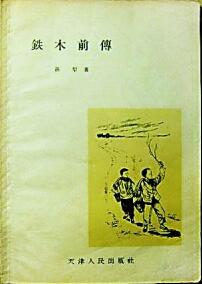
在完成《冀中一日》编辑工作后,孙犁创作了一本指导基层作者如何写作的书,名为《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1956年,这部作品改名为《文艺学习》,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13000册。多年后孙犁回忆说,这部书写下的是他对文学与生活,或者说是人民与文学之间的血肉关联的认识。在这部作品里,孙犁写下了他对何为优秀现实主义作家的理解。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完成这部书是在1942年,孙犁还没有正式开始小说创作。
在《文艺学习》中,孙犁认为,对于当时的作家而言,所要直面的,是一种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新的现实”。“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行动,确是波浪汹涌的。而且它‘波及’一切东西,无微不至。”那么,“新的现实”最重要的表征是什么呢?当然是人,“因为人是这个时代精神和行动的执行者和表现者”。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着重要改变,作为作家要深切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去表现。“以前,在庙台上,在十字街口,在学校,在村公所,上城下界,红白喜事,都有那么一批‘面子人’在那里出现、活动、讲话。这些人有的是村里最有财富的人,有的是念书人,有的是绅士,有的是流氓土棍。这些人又大半是老年人,完全是男人。”可是,在冀中解放区,一切发生了变化:“而今天跑在街上,推动工作,登台讲话,开会主席的人,多半换了一些穿短袄、粗手大脚、‘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年轻人。出现了一些女人,小孩子。一些旧人退后了,也留下一些素日办公有经验有威望的老年人。这些新人,是村庄的新台柱。以前曾淹没田野间,被人轻视,今天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上,超越那班老先生,取得人民的信赖。”
因而,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而言,重要的是,“他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他是新文学的产妇,要在挣扎战斗中尽了他的任务”。那么,如何表现新现实与新人?首先,作家要熟悉现实生活,要“深切感受到了生活的动荡,作者的感情灌注在所写的事件里,作者有概括材料、取舍材料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好的结构”。
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写作者,要融于他的时代而不能对时代漠不关心。“他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那时代、社会、人。”最为重要的是,一位作家要有总体观,体验到时代的总的精神,生活的总的动向。“因为体验到这总的精神、总的动向才能产生作品的生命,才能加深作家的思想和感情,才能使读者看到新社会的人情风习和它的演变历史。”这些看法如此透辟而有穿透力,至今读来都深具启发性。当然,这些看法也意味着孙犁开始创作之前已经有志于成为现实主义作家,他在其后的创作中践行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无数读者从这部作品里闻到了水乡清新的空气,认出了美好的家园和家人,更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孙犁希望写出人民身上非凡的勇气、坚强的信心以及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因此,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多数作家笔下破败、灰暗的乡村相比,孙犁笔下的乡土独具气度与气象。
《荷花淀》有着清新之风,孙犁在延安完成,当时正是炮火纷飞的1945年。在这部作品里,小说写出了白洋淀人的日常和水生家的安宁。“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可是美好的家园却要面临外敌入侵。水生不得不离开家去大部队了,因为,“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水生是抗日战士,作为妻子的水生嫂则深明大义,这便是战争背景下的新现实与新人。
水生嫂们来到了孙犁笔下——她们与中国以往小说中围着锅台转的、呆板而麻木的乡村妇女完全不同。她们怎么可能只是柔弱的被保护对象,她们怎么可能只会干家务?孙犁笔下的她们,开朗、明媚、乐观,有胆识,也有承担。“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小说中听到她们爽朗的笑声,感受到她们的力量。而就在水生们去抗日的那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蹬在流星一样的河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
这是独立能干的女人,她们和男人一样有力量。为什么延安战士如此热爱这部作品,为什么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像插上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因为无数读者从这部作品里闻到了水乡清新的空气,认出了美好的家园和家人,更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1956年创作的《铁木前传》中,有着中国北方农村的日常生活风貌。“在谁家院里,叮叮当当的斧凿声音,吸引了他们。他们成群结队跑了进去,那一家正在请一位木匠打造新车,或是安装门户……”“如果是在春末和夏初的日子,村里的街上,就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和一炉熊熊的火了。这叮叮当当的声音,听来更是雄壮,那一炉火看来更是旺盛,真是多远也听得见,多远也看得见啊!”
小说写下了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的友谊与疏远,写下了九儿、四儿、六儿、小满儿等年轻人的情感变化。儿时定亲的九儿和六儿的情感因时代巨变发生了改变,女青年九儿发现,爱情的结合和童年的玩伴意义完全不同,她由此看到了更广大的天地和世界——历史的变革浸润在点滴人际关系中,《铁木前传》写的是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在这部作品中,孙犁写下了中国农村社会风俗习惯的巨大改变、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他写下新环境和新景物,也写出了新的情感和新的烦恼;用笔记下,用笔画下,用笔刻下,这位作家写出了所处时代“复杂的生活变化的过程”。
《铁木前传》是明朗的,明亮的,令人鼓舞的,这部有着浓郁诗性色彩的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一经发表便引起广泛影响,被后代读者传诵至今。即使历史条件已经变迁,那热火朝天的景象,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谊,青年人之间的情愫暗生依然有着穿越时光的魅力。——孙犁小说是与时代紧密结合的,但是,多年后,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也能辨认出属于我们的痛苦和热爱,悲伤与喜悦。
孙犁写下那些新的现实和新的人民,他珍爱笔下的每一个人。作为作家,孙犁是宽厚的和体恤的,他看到人性美与人情美;他热爱和理解劳动者和农民,尽管他们可能性格上有缺陷,有令人不满意之处,但他依然愿意给予他们同情、爱与理解。这是孙犁小说人物没有概念化和脸谱化的重要原因。作为解放区走出来的作家,孙犁的写作无疑是成功的,正如学者郜元宝所指出的,“从‘五四’新文学开创以来,如此深情地赞美本国人民的人情与人性并且达到这样成功的境界,实自孙犁开始。也就是说,抗战以后涌现出来的孙犁以及和孙犁取径相似的革命作家,确实在精神谱系上刷新了中国的新文学。”
但愿人间有欢笑,不愿人间有哭声
作为小说家,孙犁有强烈的共情能力,他的作品总能与不同时代的读者凝结成坚固的“情感共同体”。他的独特处在于不以故事而以情感结构小说。晚年总结写作经验时,孙犁说,“在创作中,我倾诉了心中的郁积,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心里话。”某种意义上,孙犁成功地将革命文学、现实主义美学与抒情传统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他将抒情传统中的情与志、情与辞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因为表现了新现实,也因为表现的是新人,孙犁得以成功改变革命文学的表述方式,拓展抒情文学的写作路径,他的小说因此具有超越时间的魅力。
在历史特殊时刻,孙犁能准确感应并描绘出大变革时代普通人民的心理期许。谈及《荷花淀》何以受欢迎,他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和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的确如此,《荷花淀》中,孙犁写出了个人的思乡之情,而这种情感也代表了广大士兵及普通民众渴望战争结束、过上安宁幸福生活的愿望。换言之,孙犁作品里有专注于情感抒发的“个我”,他所要表达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与此同时,这个“个我”也是一个“公我”,他的声音同时又是广大人民的心之所愿。“个我”与“公我”情感与价值取向的高度契合是优秀革命抒情作品成功的关键,也是《荷花淀》历久弥新的原因所在。
《山地回忆》是孙犁写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篇作品,深受读者喜爱。这篇旨在书写军民鱼水情的作品,从“我”与“妞儿”的最初认识开始写起。见面并不友好,“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那个反对在上游洗脸的女孩子便是妞儿。
《山地回忆》平朴、真挚,整个故事随着人物情感而流动,从争吵开始,性格直率的妞儿后来为“我”做了双袜子,而“我”则与这家人产生了情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交情。“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从“送袜子”到买布、“做国旗”,这篇小说并没有强烈的故事冲突,但是,读者却深切感受到军民共同抗击日寇的决心以及对新中国成立的无比欢欣与热爱。小说虽然书写的是生活的“细枝末节”,但这些细节却因为真挚情感的浸润而折射出时代之光。
孙犁是对世界怀有深情爱意的写作者。即使是行军打仗途中,他对大地山河以及最普通的山花草木,都抱有深情。在晚年,他也多次怀想自己的战争岁月,表达对革命战友和解放区人民的思念。作为作家,他珍惜在艰苦岁月里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
因为对世界怀有深情厚谊,所以孙犁的作品里有一种特殊的艺术光泽。那既是出自现实世界实在的美,同时也是属于他对事物的独特理解。某种意义上,“但愿人间有欢笑,不愿人间有哭声”是这位作家的写作理想。换言之,尽管经历了生离死别与鲜血淋漓,这位作家最希望的还是在文字中展现世界的应然——他希望展现世界应该有的样子,人应该有的样子。
特别要提到孙犁对语言的敏感,他终生都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语言。在他那里,语言是作品的血脉之音,语言是内容本身。语言不仅传达故事,更传达作家的情感与美学认知。事实上,早在《文艺学习》时期孙犁就意识到:“我们要努力去找最能表现这个新生活,和这个新生活血肉交关的形式和语言。”因此,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孙犁心无旁骛地对汉语进行了耐心擦拭和打磨。他追求“一切景语皆情语”,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他追求汉语的典雅、凝练,追求汉语的音乐性与节奏感;他的文字里有属于中国美学的清新、留白与写意。
孙犁致力于将现实主义写作美学、中国抒情传统与一种雅正的汉语之美完美结合,他在《荷花淀》《铁木前传》《村歌》《山地回忆》《风云初记》这些优秀作品里践行了这样的美学追求。这是孙犁小说之所以让无数读者念念不忘,令无数后辈作家追随学习的原因所在。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22日 13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